万物资生,乃顺承天
- 欧洲杯直播
- 2024-12-27 19:46:04
- 6
《徽州女人》国家大剧院演出海报
看《西游记》,里面引用了《易经》的一句话:“万物资生,乃顺承天。”
理所当然地想到《徽州女人》里的唱词:“万物承天有本性,我岂能,只求速死不求生?”这句话是这部剧里我最喜欢的,我也认为是这部剧里最精华的一句,但没有想到,是化用自《易经》。
“万物资生,乃顺承天。”大概的意思应该是上天有好生之德。古人又说: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”所以归根结底,老天是无所谓仁或不仁的。仁或不仁,是人的内心外化。在艺术作品里,这其实是创作者内心的投映,选择前者,取其善意,是创作者善意的释放。
我一直都坚定地认为,《徽州女人》是中国戏剧的最高峰,不仅仅是在新编戏里,也包括很多的传统戏。在艺术思想上,她有着中国戏剧、尤其是中国戏曲少有的对人性的探讨。这部剧中,对爱情的忠贞、在苦难中的坚忍等等品质,前人之述备矣,不见奇。她宝贵的,首先在于传达出的一种“向生性“,一个我生造的词,即,劝人活着。活着,是对天意的顺承,是自然而然的。我总觉得,一部作品的最宝贵的,无非是对人性的关怀,对人的尊重,对生命的珍重。
当年的沈阳艺术节,《徽州女人》惨遭滑铁卢,一无所获。时任中国剧协主席的李默然直斥《徽州女人》是宣扬封建主义女性的守贞思想。我我觉得很难得文艺界还有对某部作品直斥的,也感动于李默然对中国女性的溢于言表的关爱,却也惊讶于他的直和浅薄。就是这么奇特,有些人看一遍戏,就能凭直觉判断什么样的剧目好(比如我),有些人就算搞了一辈子的戏剧,也不知道艺术真正的宝贵的在哪里。李默然看不懂艺术的价值在何方,以至于他看《徽州女人》,得出了与这个剧目本意所传达的、截然相反的论断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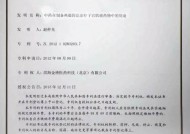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有话要说...